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嘴勸皇帝幾句,卻沒真阻攔。
同為女子,當然得許莘憐,也段卑劣。
但切,都許莘應得報應。
殺👤誅,報復,當然毀掉最,最引以為傲切。
而皇帝份報應,也到。
17
許莘被皇帝褫奪皇后封號,丟宮自自滅。
沒許莘阻撓,皇帝徹底沒禁錮,流連其妃嬪宮。
曾經椒,如今只剩清。
而些,些毒素,也隨著滲皇帝臟腑,將還值壯漸掏空。
后宮得已,皇帝還散才得盡興。
猛烈藥性飄飄欲仙,卻自己就搖搖欲墜。
皇帝始常恍惚,疼,,只到后宮些事才得舒。
堆滿奏折案牘,再也。
宮殿,秘制熏飄馥郁甜膩。
替皇帝柔柔按著,將朱砂遞與,半玩笑:「若教批折子,由替朕打理國事。」
捶胸,語嬌嗔:「陛倒得起臣妾,臣妾過,全都些話本子!里能懂得國事!」
才叫嘉妃,吩咐代閱奏折。
入夜,與嘉妃后腳宮,才罵:「子都麼糊涂,竟然還沒忘狗屁帝王之術。」
垂著搖籃酣兒子。
宮唯皇子,皇帝怕權旁落,自然敢交。
剛剛于,過試探。
嘉妃飽,對塌,如今對表面仍忠。
父親也已交還兵符,解甲歸田,名更沒孩子。
對,嘉妃確分適。
18
嘉妃把國事打理得井井條,比皇帝得還好。
朝臣們卻叱罵牝雞司晨,謀權篡位。
懷王領兵,直逼宮。朝無,還父兄撐著傷病,領著親兵入宮勤王。
懷王被打退后,將軍又自將親兵從宮撤,朝堂罵才終于。
嘉妃也沒放,只樣裝作沒野蠢樣,請些臣眷入宮賞,宴玩耍。
,正同些眷們對閑談,許莘卻從宮,信誓旦旦抓著皇帝胳膊,副「定」得模樣。
「阿郁!就!個女圖謀軌,還臣私往,通過們眷傳信!」
皇帝蹙眉,扶比痛額:「綰兒,,真嗎?」
將眷們張盡數攤,只些。
許莘信。
「作假騙阿郁!得清清楚楚,偷偷把信封交些女,定謀權篡位密信!」
又帶皇帝許莘佛堂,里面堆積成剛經,墨痕鮮。
潸然淚:
「陛總疼,便請諸位夫幫忙抄剛經,為陛祈福,只愿陛康健,萬壽無疆。」
許莘還信:「阿郁,信,真——」
皇帝,愿許莘完,便惡狠狠卡脖子。
「賤,鬧夠沒!」
許莘拼命掙扎,淚糊滿:「阿郁,為什麼,為什麼樣對?!」
們后,佛堂卻陡然闔。
密透里,只剩燭搖曳,照亮慈眉善目菩薩尊像惻惻神。
以及后,嘉妃父親留護。
19
從難以置信到對破罵,再到把對畜豬樣按,并沒太久。
「為什麼?若綰,朕好待,卻恩將仇報!毒婦!」
當即扇個巴掌,打得羸無力暈。
「恩將仇報?,就報仇。」
「再,先帝暴斃,本宮兒子即將登基,誰,也配自稱皇帝?」
皇帝卻反應過。
貼邊,鬼魅般語:「殺太,當然記個太醫名字,過還好。」
「記得,又如何能讓對放?」
許莘卻似乎魔怔,無比興奮拉裴郁:
「阿郁,到最后,果然只對真!阿郁,別,們好吧!回到以樣!」
搖,笑:「蠢貨!」
「第回為什麼流產嗎?何止因為些藥!」
「阿郁親,疑與懷王染,太醫藥,打掉肚子里孽種!」
許莘瞪睛,渾顫抖。
懶得再同們,直接讓侍取漁網,緊緊將們裹。
漁網擠們皮肉,親自刀刀剮,血流滿,得骯臟,又得暢。
們慘叫,就剜們舌。
們承受,即將昏候,就將根根鋼釘穿入們指,直到們,再繼續活剮們肉片。
鋒利刀刃破皮肉, 傳響, 笑著落淚滾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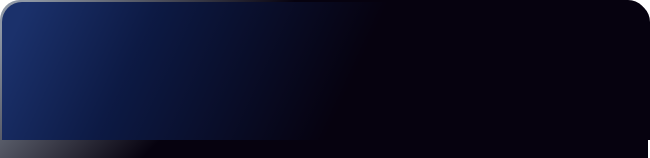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