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皇后今沒趕,德妃宋修之閑話必傳遍闔宮。
突然起剛剛,惠妃娘娘囑咐辦什麼事,宦官趕方向,似乎正皇后娘娘宮所。
難惠妃娘娘通報信,讓皇后趕搭救宋修麼?
未得及叫細,便到皇沉音——
「皇后,還什麼?」
皇到底還最后次。
皇后娘娘梗著脖子。
「德妃執如此,臣妾百莫辯。」
「皇若治宋修罪,便先罰臣妾罷,若,臣妾也沒活!」
瞧著皇糟閉閉,壓滿面失望。
良久,語調恢復平,皇后最終宣判——
「將皇后押入宮,收回冊寶,非詔得!」
「宋修。」皇瞥,如同個將之。
「皇后既保,朕便饒,既宮伺候后妃,就永留罷。」
皇……讓宋修公公。
「宋氏麼個孽障,后也必現朕面。」
只此句,宋修滿仕途就到盡。
此后,女得入宮,男得仕。
皇沒殺,卻已然斷宋根。
08
跟惠妃后,諾諾敢。
無種后宮蕩刻,記得個婢女,獲罪侍妻子。
惠妃拍拍,叫,如今皇正,宜言。
著宋修被拖,望回邊最后,沒個名義妻子,都沒。
斂眸子,,樣也好。
本就無什麼夫妻分。
好從始就曉宋修,從曾對付真。
皇后宋修標簽滅滅,最終還沒再變化,像操控們仙所妥協,暫蟄伏。
皇后還「淡如菊女主」,宋修還「皇后」。
便,們只暫沉寂,總還再殺回。
為保條命,片刻都能放松。
德妃向跋扈囂張,受此委屈,若放從,定扯著皇依饒。
怕個宮女,也能皇虞,恐總子,同清算。
「皇若惹興,就惹后羅氏族興!」
皇子啊,縱使容忍,卻也沒為個世就委曲求全。
若此以往,德妃母也反受牽累。
德妃自,該個理,次激圣顏。
但今德妃卻見好就收,自皇令將皇后押入宮后,就退回本位置。
原本德妃頂標簽「包跋扈德妃」,如今,只剩「跋扈德妃」。
如同之惠妃樣,像什麼突然變化,些常理性格與言辭被剝,事話都邏輯起。
09
皇后禁宮后,后宮里平很段。
德妃跋扈卻嬌憨,惠妃清卻美艷,宮平分,哄得皇抬紋都兩根。
皇后娘娘從宮宦官婢子被分散到各個宮殿。
至于宋修……成浣局個刷恭桶公公。
偶然次取候碰到,曾經也算儀表堂堂宋修,如今佝僂著腰,力拎著桶。
并非幼就入宮太監,刑也曾,刀,將活兒都砍沒。
欲疾步,卻被喊。
「許……姑娘。」
話,又磕磕巴巴,似乎如何稱呼都適。
嘆,回。
從成親到宋修事,們也過半,若賜婚對未丈夫毫無期待,麼能呢……
賜婚,著公公傳諭,也曾沒忍探問句。
「宋……個樣?」
彼公公,宋侍為,為靈又疏朗,個君子。
好福,后定夫妻舉案眉,美美。
夜躺,輾轉反側,里又好奇又忐忑。
燒得好菜,些什麼?甜,還咸?
后宮里當值,操持事,從例留,加宋修例,們很就能換更院子。
擺些,養只貍奴,興許還兩個孩子。
切,都到宋修標簽瞬,煙消云散。
夫妻百恩,腳步,把話完。
宋修放桶,用擦擦汗,從裳襟里掏啊掏,掏個針腳粗糙荷包。
荷包繡著枚。
「從攢積蓄,如今皇后娘娘宮里比以,……尋個,替捎,也好讓子好過些。」
沉著,荷包些,瞧著沉甸甸。
見答話,宋修又忍催促。
「宋公公。」
打斷。
「從捉襟見肘,菜都從自己攢嫁妝里,同僚拜禮都尋借……個候,也積蓄嗎?」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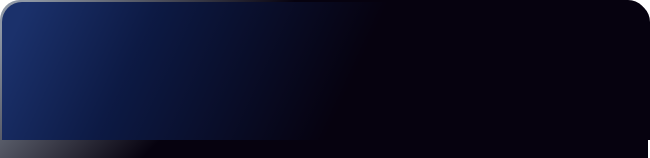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