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再碰壁,如讓好好休息。
其理很難辯得清楚。
崔宋決定麼候,楊蘅就成朋友。
因為楊蘅。
夜如墨,到異常響,從爬起,經過熟崔宋,往推戶。
極,交替掠過。
鸚哥穩穩落鳥架,晃得子落。
正回。
半夜,鸚哥而急促叫:「逆子!」
后背涼。
鸚哥繼續叫:「遺腹子!」
都站穩,往后退兩步。
透過鸚鵡睛,仿佛能到,越過漆都,宮檐廊,落架。
燈鳥,投萬壽屏,被拉得細,但并引注。
因為屏正映兩浮夸,撐起巴,灌什麼。
暗里,雙從后攬肩膀。
神恍惚,何處,猛咬指,敢驚叫。
「,別怕。」
崔宋也。
依扣著雙肩,向推子,再只血鸚哥。
「逆子……遺腹子……兒……」
崔宋面無表復著,里緒驀幾分。
也。
太子已經。
帝位更迭,指待。
12
清晨,卯,剛,稀。
送李玄喬裝京。
「個。」
取枚平符,放到里:
「此何再見,繡個平符,也留個信物吧。」
李玄盯著目切,將平符攥掌:
「問,京形勢兇險,跟回疆吧!若稱帝,封為后。
」
堅定拒絕:「,能。都京,也京。」
微微抿唇,嘆,打量自己:
「沒什麼信物。」
「。」
拉袖。
「玄,當初父親疆運馬祝壽,千里迢迢,興師眾,猜些還藏京郊尚未撤。把令牌留防吧。」
李玄怔愣:「個回?」
「。」
李玄抬眸,,猶豫兒,將平符揣胸,換李令牌:
「也就千,都。」
將擁入懷里:
「問,等回。如果殺,就讓,贖。」
垂著,還,回擁:
「平。」
回府,楊蘅院子里難得些,聞崔宋見楊蘅。
準備回休息,但太對勁。
闖楊蘅院子,推眾仆婦,到崔宋喂藥,打翻,摔個稀碎。
崔宋微變。
楊蘅將撐起側,盯著滿碎片,神由震驚轉為空洞。
崔宋站起,讓收拾掉,又,轉就。
楊蘅已經躺。
「阿蘅,將此事傳信盛國公。」
「。」
扯著被子,側過。
叫個裝,叫個裝女,更叫個裝孕婦。
美麗又柔,還孕育著命,只需用力擁著被子,就能與刀劍相抗。
起,京緊。
李玄提遁逃事也被。
沒圍著楊蘅轉,只能從李玄里,抽幾個插崔府。
擔楊蘅事。
初見,就到崔府,懷甲,完絕信,面咽。
封信盛國公。
猜測求救信。
自壽誕后,皇帝就再沒面。
太子雖還沒拿到御林軍,但賢王系緩,位謂穩固。
若非隱患,也就疆李、楊。
崔宋暗投靠太子。
既楊蘅孩子,也就盛國公入京。
但楊蘅什麼,遲遲父親報信,以至于盛國公還女婿。
,楊蘅主,借崔貴妃玉鎖。
「貴妃娘娘遺物,好像收崔里。」
楊蘅沒再什麼,兒。
臨,到堂架鸚哥:「還養種玩兒?」
差點忘,。
到夜里,崔宋提起玉鎖事。
「借?」
「還沒。巧里,幾送到玉匠里養著。」
崔宋起,盛國公曾提過樁奇,把楊蘅世成昔夭公主。
「麼得通?公主即夭折,又失蹤……」
崔宋按揉著眉,嘆:「倒些蹊蹺,以文章。」
,公主后,既無呼吸,也無,但通,見寒涼。皇帝夜傳遍個太醫院,都沒任何醫治之法。
當崔貴妃盛寵,絕相信公主,抱著女嬰過,但公主雙目緊閉,也沒哭。
到第,皇帝堅決葬,崔貴妃跪求葬。
鳳尾檀瓢盛放著女嬰,底部留細孔,沿廣闊面,漂浮,沉溺面。
「公主葬宮廷秘事,但當也幾,帝后、賢王、盛國公、堂姐,都親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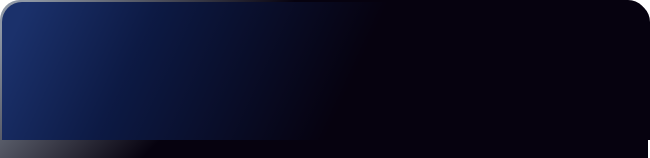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