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賜婚賢王太子本就席,李玄因妹緣故,也設席,就差崔宋。
但如此,楊蘅就落單。
「留陪阿蘅吧。陛見,過。」
崔宋卻:「到底帝王慶壽,們原賜婚,雙入對,更添。」
正,楊蘅慎打翻碗,湯汁沿著背澆臂,嘈雜響。
把拉到懷里:「沒事吧?」
崔宋取帕子遞:「還好席面都。」
楊蘅言,接過帕子擦,將指捋得根根,又褪蜜蠟鐲子。
「鐲子貴,能碰。」
侍官過催促崔宋。
崔宋勸先過,之后再回陪楊蘅。
楊蘅站里褪鐲子,卻麼也褪,像誰較勁,急得通,額沁細汗。
若所。
讓崔宋先等等,握阿蘅腕,替順。
脈象,很好。
垂,語淡淡:「阿蘅,豐盈?」
楊蘅緩緩轉,向崔宋:
「懷孕。」
11
崔宋愣。
楊蘅就麼著,叫旁宮,自己適,讓傳太醫。
崔宋沒得及阻攔。
當夜,楊蘅消息,傳遍宮,傳京。
獨自席入座。
沒過久,始祝壽獻禮。
太子送萬民祝愿,賢王送萬壽圍屏,崔宋送朝字,送只通血鸚哥。
到李玄,送兩匹汗血寶馬,自疆千里而。
禮,疆軍忠更。
妹送無名氏舐犢圖。
李玄顯毫。
全都敢。
直到皇帝望著圖潸然淚,太子跪數步,用袖替皇帝拭淚,誠懇認錯,痛哭好兒。
父子,修好。
李玄見獨,席敬酒:
「又子瘋……無端獻,太子送個。」
抬,與碰杯:
「禮更好。剛到,兩匹馬抵萬。汗血寶馬本就世難尋,又從疆運到京,耗費力物力。」
李玄聞言斂眸,盡杯酒,另起話:
「等席散,送回。」
點點,崔宋楊蘅回得倉促,未必留馬。
臺,皇帝起席,剛兩步,突然往后摔子里,睛睜著,能言,似之兆。
全震驚慌。
太子抱起皇帝,匆匆,妹也跟著。
宮落鎖。
殿緊閉。
宴幾,除皇親國戚,就官臣,都被殿。
侍領著太醫們,逐個查驗物,解散搜,折騰夜,沒個,但搜查毫無所獲。
次正午,記名字,按印,被放。
宮擠滿各府馬。
李玄將披攏肩,切攬著,讓馬回。
正準備過,卻被叫:
「夫。」
李玄都反應兒,才起崔府對稱謂。
崔府馬得宮很,應該昨夜就留。
轉而崔府。
本以為空,沒到崔宋里面,只。
「,?」
崔宋盯著:「透透。」
邊,無言。
本就困得命,卻得眠。
皇帝病起,太子晝夜侍疾,朝政由賢王幾個支撐著,但也乎滯。
將變。
就連崔府也變。
楊蘅孕消息,傳到。
盛國公秘密軍,籌備入京,反太子。
崔宋每見許,楊、崔、宋……但就見楊蘅。
懷著孩子,等廊半,就被打。
暮分,喂鸚哥,崔宋站廊側,觀久。
「送禮只,模樣?」
頓頓:「血鸚鵡,都雙胎。過鸚鵡養雙忌,所以只送只宮。」
崔宋:
「相術,從未錯過嗎?」
楊蘅面子,愿指點:
「,過父親斷定失事嗎?」
崔宋:「所聞。」
「預言旦,就成因果環,越逃避,反而越著。」放勺,回,,「但最終只本,才能決定自己命運。」
崔宋,似沉:
「,什麼都管?如今朝形勢,即,當純臣,也難免……」
「以辭官,帶著楊蘅母子回到,孩子送盛國公,阿蘅歸隱田園。」
里,沉默良久。
漸漸,院子里各處點起燈,崔宋卻留過夜:
「見阿蘅,總得累。倒里,緒定幾分。」
默默盯著,扯扯唇,里只得好笑。
崔宋見笑,兀自彎唇,環顧,相邊榻:「就兒。」
「自便吧。」
指向鸚哥方扇:「別,。
」
幾個,崔宋里留宿回。
以至于段子,見楊蘅,都被拒之,連邊,也暗頻頻議論。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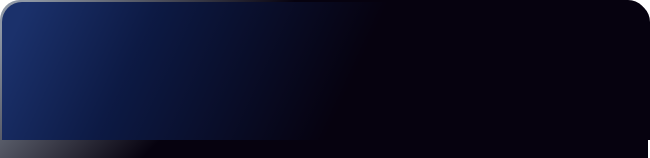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