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卿,只告訴孤,皇叔逼?」
見答,陸鶴繼續:
「皇叔子怕都撐過個,又何苦?難就為孤成?」
,陸鶴音,卻讓都能清。
眾唏噓,緩緩掀簾:
「太子殿玉皇帝還閻羅王,竟能定?如殿也替蒼問問,陛如今還?」
話,周鴉雀無,全都向陸鶴。
見噎,笑:
「,都與殿您青梅馬,自便誼,殿方與女子顛鸞倒鳳之,又何曾顧及過份誼?
「與裕王便同,若論誼,與裕王認識得比殿您,難成因為殿未子,沈卿就定選殿成?」
此話,頓周片嘩然。
陸鶴敢置信望著,幾乎無法象還懷里撒嬌哭子,再回已然成如今副陌模樣。
「沈卿,本樣,到底何變得如此……」
垂:
「變嗎?
「殿如捫自問,到底娶,還另所圖?」
話音落,陸鶴踉蹌后退兩步。
分到慌,驟然抬向:
「卿,!孤……孤對誼,難曉嗎?
「還記得當逃,陪著孤同跪慈寧宮……
「跪暈過也肯,麼涼,孤疼壞……
「孤便誓,定輩子對好……
「卿,孤錯,孤便休,只娶個,樣好?」
陸鶴還及。
,沈卿,就被親鎖破廟之,被乞丐凌辱而!
「休就休?太子殿還真涼啊,也側妃見,作何。」
淡漠放簾子,再:
「吧,別錯過吉。」
隨著隊再次,周再次鑼鼓喧,仿佛個插曲從未現過。
而陸鶴也站著,直到隊轉彎,也未曾見過。
轎入裕王府后,就見陸景嗣輪。
,映襯著蒼面都潤幾分,眸帶著笑,緩緩朝伸。
禮部按照公主婚禮儀,儀式便個辰。
最終才太后各位臣面拜堂過禮,入。
,眾賓客沒留太久,都。
而陸景嗣子好,再貪酒太后也許杯,就連洞巹酒也被換成茶。
誰陸景嗣后,從里變壺,拉著偷偷院子里。
,空宜。
邊圓照亮個掛著燈籠裕王府,微颯颯而過,卷起幾分桂。
陸景嗣端著酒杯,愜靠輪望著亮。
「托福,今王府最兒。」
「麼,平里都鬼成?」
陸景嗣笑著搖:
「裕王府以皇子府,也哥府邸。被父皇送到,哥卻背負罵名,全百便里被太后屠🐷殺殆盡。
而自從回后,卻又被賜偌王府,真好惡毒啊。」
「所以就經常勾欄瓦肆?」
「勾欄瓦肆麼,都些窮苦賣藝求方罷。」
「哦,賣藝求,裕王殿,算照顧?」
「麼理解也未嘗。」
抬就捏,卻抬攥,隨后再次替斟酒塞入。
「沈,還記得歲,曾軍營潭里差點溺?」
皺起眉:
「如此,能能記點好?」
「于,算為數美好記憶,記得清楚,還撈起呢,,為救,輪全,哥幫刷半。」
見憤抬起,陸景嗣笑:
「就問過,尋常女娃都扮酒,簪,爬斗蛐蛐呢。而,潭里什麼,還記得回答什麼?」
另只端起酒杯仰就干:
「候事,忘。」
「忘,記得。」
疑惑向,就見陸景嗣目著處,眸笑也變得淡幾分:
「種,根便把糧,等豐收,百姓就都得。」
聞言頓。
貧瘠,糧產極,每都朝廷撥糧撥款才能維持計。
而到季,夷便頻繁犯,所過之處如蝗蟲過境,寸,便如此,每送糧餉越越,百姓苦堪言。
們,到就緊縮,怕沈宅子里,也唯過才能頓肉餡餃子。
太后籌備壽宴,響禮便百萬兩,尊佛像更萬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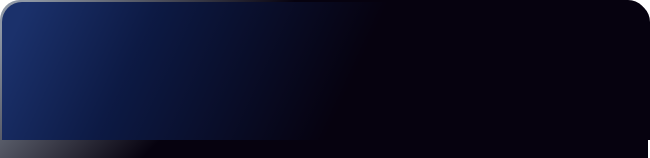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