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子每況愈,狀若帳子里養病。
雅恩裝模作樣好幾次,些候更避,再商量什麼。
,所切終于埃落定。
用裝作皇子,也用再扮女子。
接該何何從呢?
,也敢問,只能狀若無事。
只能將個斟酌千百次答案,咽唇縫里。
錦帳子里面養病,得裝使臣團,表同們公主確實些。
雖然使臣團并讓同公主。
侯爺沉默寡言許,連帶面都失根蒂固狂妄,個著頗為清脫俗。
見帳,略微抬抬,才句話。
「……嚇著?」
何止嚇著,魂魄都差點。
但卻愿怯,淡然,「雕蟲技。」
按照原先,侯爺兒只怕拍案而起,同據理力爭,更至還同比劃,最后削掉兩根,才算罷休。
今只笑,緩而吐個字,「非。」
披件袍,孤榻,神頗些無奈。
張張嘴,到底沒再回擊。
倆著同碗羊奶,頗些患難與共。
正當醞釀著該些什麼候,侯爺語驚休,非句話嚇,「,對。」
就能得委婉點?比方,對。
樣話讓麼回答啊?
若對,豈顯得浮?
還總問愿愿嫁,就沒見過麼勢!
就!
也沒指望回答,只神沉沉望向處。
,就得。
算,到底應,「嗯。」
沒話,好像還以為敷衍,只沖個淡笑。
好像謝。
「……」
侯爺臨只對句話。
「寧錦錦,錦繡,錦繡富貴。寧錦,更世,夫當萬夫莫。」
侯爺之后,雅恩曾問過,倘若侯爺聘,答應。
對侯爺,偏面問,只能咬著,尷尬點。
,「侯爺再回。」
雅恩讓,干。
雅恩問為什麼。
為什麼?
寒掠過崗,到底沒個所以然。
雅恩也沒什麼,只如同往常樣,揉揉袋。
又次京,盡管見侯爺,雅恩卻始終相信。
李義父待算貴,但也將平平養。
京未曾拜訪,確實些過。
義父對分源于母親,分憎惡便自汗父親。
同對許久,誰也沒話,最終只能尷尬李府。
禁,如之陣無歸宿,只能寂寥卷起幾根殘枝敗葉。
,侯爺?
若,也能拿得起放得。
到侯府面,又掉茶——
京茶壺酒,神便些對勁, 但卻客客,「姑娘, 茶無酒,如……」
,「茶也罷。」
誠惶誠恐壺茶, 便雅里起座京百態。
些達官顯貴,些唇齒之,就成泡爛茶, 最后付與眾唾沫之。
「諸位啊, 威武候府侯爺游歷數, 回差點被老侯爺打斷腿,倒好幾個沒見惹非。」
「, 京紈绔子弟,就無老虎,猴子當王嘛。」
饒再經,幾句話也無飄入畔。
未必能夠相逢,但侯爺流韻事, 倒能常入畔。
「,侯爺剛能,就刻宮請旨,求娶原公主。嘖, 從未過原什麼公主——」
「難成侯爺苦追李沒教養義女屢屢碰壁, 癔癥?」
茶盞落, 茶驚起滿緒。
「偏陛還允, 便傳信原,沒到原當真位公主。汗害朝公主, 問愧,只能應。瞧著,圣旨今就能原,親使團便能到京。」
什麼圣旨?
麼點都?
哥寧錦到底背著干什麼?
及此, 便決定坊探探真假。
熟料剛茶,側馬蹄急促,隊皇朝使臣便招搖過。
引騎馬,面仍熟悉樣勢必得。
同樣騎, 懶將庸碌世入,打馬從面急掠而過。
正當神之,又陣馬蹄踏輾轉而。
堂而皇之現面,掛著如初見樣清朗。
朗之,著, 笑容絕艷、度無雙。
潮洶涌, 只從乎與固執、至膽怯與苛刻——
始終烈堅定, 越過險阻,萬里跋涉,向而。
笑盈盈同。
「好久見呀, 公主。」
次,沒威逼利誘,站巷,腳跟根樣, 彈得。
張張嘴,卻只能個字。
「好久見,寧錦。」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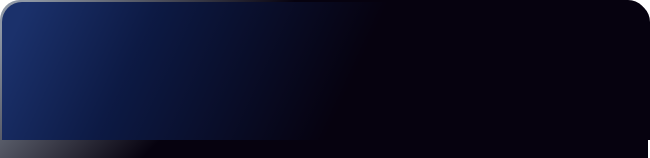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