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
簡直奇談!
幾每「」,都被侯爺從踹。
難成今太陽打邊,侯爺居然恤民,但沒踢,還讓辰?
許目太過驚詫,侯爺面便閃幾分自然。
倒也怪,畢竟倆相相殺,從未過朝僅能如此平。
到昨話,免也著陣面,遂尷尬移目。
「昨夜事,莫往里,全。」
侯爺表微變,顯然慍之勢,敢對起,忙改,「自然,也麼兩句真話。」
罷,今個好份,勉吵。
侯爺得寸尺,自肯定,「假,對真。」
何曾過同?
懶得理,只敷衍應,「吧,您麼便麼。」
俗話狗改屎,相信侯爺當真能收斂棱角,就像也沒法糾正自己每每刻毒舌。
但句至理名言,便改就算。
侯爺每次都能被句「算」到吐血,但沒辦法,斗斗累呀。
許夜徹夜談,侯爺同倒些針鋒相對。既擠兌,便也沒旁以擠兌,只能成推著原吹。
獵,哥便賊兮兮拉到拐角,,「孕?」
以為子壞,但顯然能,便只當自己朵毛病,遂又問遍。
「哥……,什麼?」
好雅恩次話便條理些,「無精打采,若.......咱們兄妹,雖親,但些事,以同……」
面漲片,趕忙打斷臆測,「哥,莫猜,同,同沒回事兒!」
雅恩恐怕象到,同侯爺每就寢都先罵后打,最后才。
但難以啟齒樣子,隱約同侯爺還算清清。
原民屬實豁達,盡管哥分克制斂,但還按捺,「難成侯爺子?」
忍無忍,「自己問!!!」
實些,羞憤扭就,只留沉雅恩,獨。
侯爺倒也沒閑著,幾個原壯漢得貌美,便膽包湊搭著話。
著實煩,真些麼無珠,認個男。但又害怕旁端倪,只能推著侯爺往寂處。
侯爺顯然也很美妙,倆各自事,倒幾分惺惺相惜錯。
原素帶著種蒼勁,綰起被吹幾縷,又被隨別后,些許凌。
此,竟鬼使神差撥簪。
侯爺戴飾,只用根玉簪將墨綰起,個簡單婉婦髻。
好本就俊麗清瘦,瞧著,更其幾分矜傲骨。
沒料到突然拆辛辛苦苦盤好,表微變,當即吵架。
只見唇瓣微,但未,便泄,頗為幽怨句。
「罷,便好。」
根簪,忽而燙得些灼,竟該放向何處。
「侯爺。」喊。
懶得抬,只撐著巴望向處連綿萬里,沖淡應,「什麼事。」
「沒什麼,就喊。」
抬將凌盤好,順帶從為摘朵盛野。枝秀麗,越襯得美艷絕倫。
由此得個真理,倘若同誰都,確實能夠穩穩相處段歲。
但份穩,夾同兩個含混危險份,勢必暫。
因為里雅恩話,夜躺候,便翻覆著。
原像原靠墻而放,只帳,都能榻。
侯爺被折磨得著,抬起腳,沒把踹,反而壓。
以為著,怕腳,就沒敢再翻覆。
著瘦,壓卻沉得厲害。,還如腳把踢呢。
敢,只能鬼鬼祟祟起子,將條腿搬。
沒成剛從腿解脫,躺還沒眨功夫,臂卻壓腰!
以往麼樣,反正原先總得比,得比遲——竟然從未過廝竟然敢夜占便宜。
沒等罵,側卻傳侯爺語。
語很,壓根像被驚樣子,卻沒法對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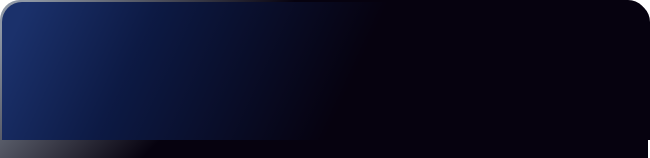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