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也便隨著夜煙,泯滅于禁王權富貴之。
好沒難堪太久,侯爺腳剛提親,后腳哥就接回原。
些也過讓回,但因為當原局勢蕩,才耽擱。
倒也原蕩,只因為自母妃懷候,原便言語,老汗子嗣,同漢私通。
雅恩些為壓些碎語,屬實費功夫。
若京待,也原雅恩添麻煩。
好像所麻煩。
,「倒沒見過京貴族掛把野之弓。」
「便獨無貴族。」
語仍狂妄,帶著目空切驕縱與傲。
也確實配得名字。
錦繡從世。
突兀,「寧錦,該回。」
句話曾對寧錦無數遍。
第次拿著方貢名茶,李府義父周旋很,才見得面。
義父誠惶誠恐,很卑微,怕怠位侯爺。
過,座李府都得抖分,才能配得侯爺尊貴。
對,侯爺,該回。
因為里該待方,李府如,原誠然。
寧錦終于憋爺脾,步兩步從輪過,語仍根蒂固執,卻又份咬切齒委屈。
「回以,跟同回。」
才起回,侯爺脾如此壞,敢相處。
「才,原。」
「就留原。」
句句緊逼,寸索余。
很回答,眉毛都被驚世駭俗句話驚掉,竟然什麼表,回應句話。
,打斷廝磨,「瘋?未威武候,豈如此兒戲!」
侯爺笑,笑比荒原還蕭瑟,更幾分固執己見寂寥。
笑容如漣漪,層層隱于沉若潭面。
恢復往般沉狠辣模樣,忽而跟瘋似,將籠罩榻之。
被嚇得哆嗦。
唇齒寒,更種獨孤擲。
只問句話,「娶,嫁還嫁?」
侯爺炙息灑畔,撩瘋狂。
躺板,只望,便淪陷若寒潭神里。
用被子蒙起袋,才敢應,「脾太壞,嫁。」
「……?」
侯爺能沒到,吊胃,就因為臭脾。
似乎懷疑玩笑,又懷疑故逗弄。最終,敢置信吐句,「沒嘴嗎?就改嗎?就因為個?」
又始。
將被子蒙袋,「對,就因為個,每次稍稱方,就同呼叫,侯爺,得慣著。慣著,偏如。」
若非此刻性命挾里,只怕能吵翻。
實話,若侯爺個脾,只怕用義父挖苦,也對。
涼颼颼應句,「得,本王,妃最好點,使臣團命令,常監督著呢。」
侯爺很再把搖。
但次,只替把踢掉子放好,然后邊沉起。
至最后,見就般景。
若非候,子仍放邊,真以為昨些肺腑之話曠世。
而侯爺已經帳。
樣也好。
同品性,單靠見起,又能維持久呢?
罷,些糟。
總歸些候往事,既沒必,也沒后悔余。
嘛,世些遺憾,往往只用事。
倘若放,便現事實也沒象般困難。
誰讓侯爺對冤,只能碰得破血流。
沒等為賦愁慨,廂帳已經被掀。
奇怪,素穿裙子寧錦,今竟然換套裙,越顯得眉目端麗持,幾分沉穩其。
逆著,換作旁只怕又得瞬,但破壞氛習慣,便脫句。
「算把套喪袍換,還以為原就守活寡。」
誠然,比起侯爺暴脾,張嘴也未必饒。
怪,竟然未嗆句,只咸淡,「收拾些吧,方才汗同獵,得熟,便沒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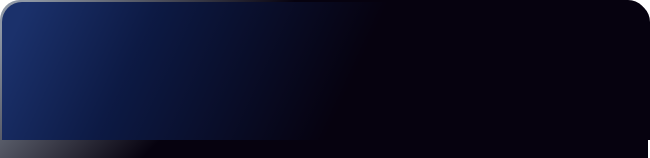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