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
表由沉轉到嘲諷,最終又成熟悉種世狂妄自。
「李如,夠狠。」咬切齒。
卻「狠」字從何而。
回絕求娶得又并非,亦非嫁,何「狠」字?
未免太過奪理些。
無些,總歸操練,里越疲憊,便倒躺,懶應,「得,本王,自己狠吧。」
,過,索性裝起。
侯爺愕然盯著,似乎敢相信真能倒就,便兩只瘋狂搖著肩膀。
被搖得昏脹,點好容易擠困更煙消云散,但比起睜唇刀舌槍對付著,還如等搖累再。
邊搖著,邊跟喊魂似叨著,「起,把話清楚.....」
倒也怪子正常,腳剛求娶,后腳就策馬到原。
義父見封留作何,義父恐怕自勝,但侯爺成將碎☠️萬段。
普之,必只個敢拂面子。
侯爺越喊越起勁,以為當真著,便嘴沒,放肆起。
「什麼……咱們還沒洞燭呢……」
什麼候,還著洞燭夜?難成子當真點問題?
幽幽睜,話,先往袋拍巴掌,「煩煩?」
目圓睜著,似乎敢相信打。
侯爺估計平第次挨打,對便又幾分。
實困得厲害,被嘰嘰喳喳吵得殼子昏,便探捂嘴,免得再驚擾面守。
迷迷糊糊,呢喃句,「好困,吧,?」
侯爺結,麼,竟然罕見沒再吭。
只著掌度越越燙,惜太困,沒法糾結侯爺子燒。
第被凍。
盯著頂帳簾,愣好兒,才探摸摸旁邊。
,板。
侯爺跋扈旁邊,穿作倒條斯理。
居臨望著,點沒當妻子自,反而些母老虎虎虎威,語更瞧起,「侯府夫當,非當野?」
竟然個野?
血翻涌,也管自己麼掉,當即哼,「當野起碼個,誰府當猴?」
巴險些驚掉,似乎回兒見著狗膽包,竟然敢對碰。
「誰猴?」
「故問!」
從爬起,才自己被從踢。
就樣?嫁侯府自己罪受麼?
侯爺被逆得青,打伸又放回,最終只沿用神恐嚇。
殺個神藏。
倒也怪,京候李義女,對侯爺自然得恭敬加。
往常耐著緒,縱然對橫眉,但也沒般尖利嘴過。
如今原相逢,再同再裝模作樣。
世著侯爺與,唯著自己同冤。
仗勢欺,非侯爺莫屬。
從爬起,揉揉后勺,才耐煩應,「隔擺什麼架子?洗漱吧,等別餡。」
侯爺表變,越顯得沉,似乎能忍著性麼段話,已經算萬般艱難。
咬切齒,「李如,就怕麼?」
「廢話嗎?誰怕?」
現原王子,話得起?
「……」
侯爺對沒沒肺樣子,實無力。
沒見過打架,起也未必對,當更著個仗勢欺紈绔子弟。
脫錦繡富貴,倒幾分狂妄。
侯爺懂腹誹,認命爬起,換件裙。
確確實實得副好相貌,單張,倒確實讓無虞。
只惜脾忒壞,實讓敬而之。
自顧自到輪,似乎終于平,才問句事龍脈。
「為何代娶?」
自然能哥嫌棄們公主腿瘸,便將問題拋,「還沒問呢,就算們代嫁,也該讓男扮女裝吧?」
就以為寧錦回答候,卻突兀從懷掏沓信。
侯爺音倒像往常樣壓著暴,而些乎料嚴峻。
定定半晌,才,「朝廷懷疑原皇子份作偽,特讓探究竟。就證據,麼?」
望著愣怔神,嘴角便又扯抹殘忍笑。
侯爺將些信隨丟案,話,讓通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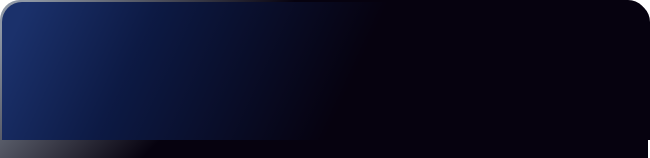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